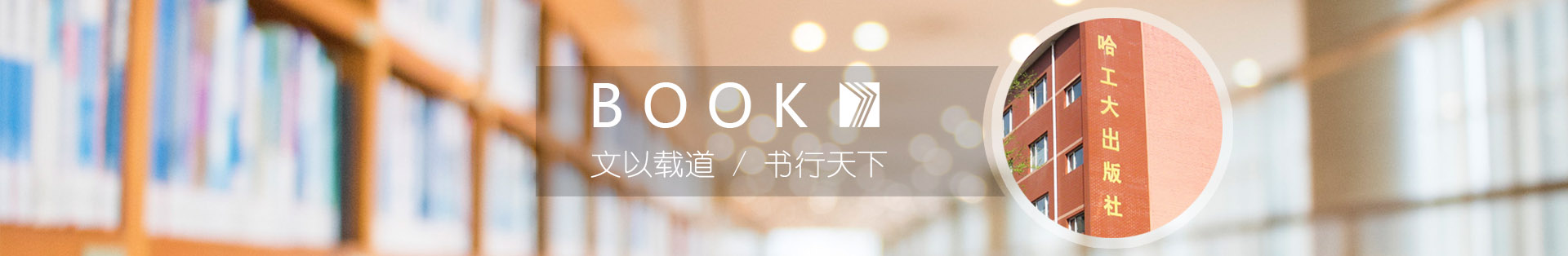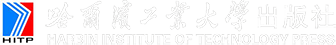《儿童科学文艺的发展历程》
任继敏
晚清至“五四”时期,梁启超、鲁迅等先贤曾大量地翻译西欧的科幻小说,当时对science fiction的译称是“科学小说”,这个命名在中国流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。当时不少中国作家尝试着模仿撰写科学小说,但因为缺乏工业文明的土壤,当时的科学小说虽然具有某些科幻因素,一部分却成了中国古代神怪小说的一种变体,如张小山的《年大将军平西传》、俞万春的《荡寇志》、包天笑的《空中战争未来记》等,以离奇的高科技武器作为法宝;另一部分却走向政治小说与理想小说的偏路,如梁启超的《新中国未来记》、陆士谔的《新中国》、春帆的《未来世界》等,借科学幻想的形式,寄寓对中国未来国家形态的政治展望。以今天对科学文艺作品的理解,以上作品算不上真正的科学文艺作品,但也算是中国科学文艺的先声。
20世纪90年代以后,新一代科幻作家创作了大量主题严肃、立意深远又具有思辨色彩的科幻作品,中国科学文艺摆脱了幼儿科普读物的定位。2015年,刘慈欣的《三体》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,2016年,郝景芳又凭借《北京折叠》获得世界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,除了获得雨果奖的刘慈欣、郝景芳之外,还有王晋康、何夕、韩松、赵海虹、陈楸帆等科幻作家崭露头角。这些作家在改革开放后直接对接西方科幻小说,他们的作品有两个重要的转变。一是以自然宇宙为描写对象,不再单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,而是转向描绘大自然与人的复杂关系,他们的科学幻想也不再拘泥于现有的科学发现和成就。刘慈欣的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、王晋康的《天父地母》等作品都将人类文明浓缩成一个整体形象,以宇宙为参照系来表现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之间的沟通、碰撞、冲突、制衡,充满悲怆、精致的史诗般美感。另一个转变是对待科技与人类社会的态度,不再是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式天真乐观的向往,而是转而描写科技泛滥带来的极端环境和社会形态,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人类的行为模式、价值取向与道德体系的转变。刘慈欣的《超新星纪元》等作品都是从自然科学推演到社会科学层面的眺望与思考。这两大转变使得中国科学文艺对人类文明与科技发展、大自然等的各方面关系的思考已经脱离叶永烈时代的科幻理论。
中国科学文艺曲折演进近百年,大体可以归为3个阶段:首先,在对西方科学文艺作品的译介和仿作中形成了初貌。其次,与苏联科学文艺理论的互动中实现自我命名。最后,观照本土资源,与世界科幻潮流走向融合。《三体》和《北京折叠》夺得雨果奖并不是偶然,其说明中国科学文艺已经具备跨越文化藩篱的特质。刘慈欣和郝景芳的科幻创作均在兼顾科学逻辑与艺术想象的同时,融入中国历史情境与社会现实的意象。这也为中国科学文艺指明了一条道路,即用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对科技发展下人类社会、文明状貌、个人命运进行先验描摹,以展开对人类文明共同体终极归宿的思考。(王洁.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及三大走向.江西社会科学.2018,38(7):99-105.)